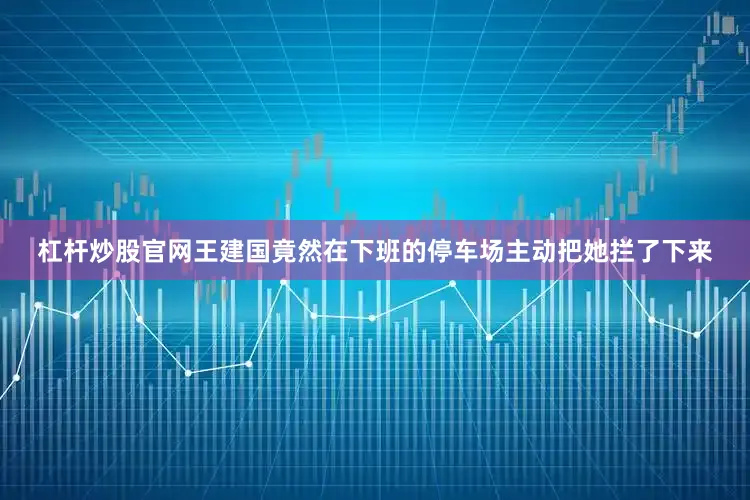
那辆从主任手里贱卖的奥迪,后备箱里藏着改变我们一生的秘密

“李诚!你快过来!”
苏晴的声音站在院子里,带着一种压不住的、混合着激动和恐惧的颤抖。
她刚把那辆从领导手里买来的二手奥迪开回来,正准备把车里收拾一下,谁知道一打开后备箱,角落里一块蒙着厚厚灰尘的布就吸引了她的注意。她起初以为是块没用的破垫子,想顺手拎出来扔掉,结果一拽,才发现布底下沉甸甸地包着一个老式木匣子,边角都磨平了,看着就有些年头。
正在洗车的工人也看愣了,连手里的高压水枪都忘了关。苏晴蹲下身,小心翼翼地揭开那层灰布,在沉重的盒盖被打开的一瞬间,一股浓郁到近乎凝固的酒香,毫无征兆地扑面而来。
匣子里,整整齐齐地躺着两瓶酒,瓶身已经泛黄,红色的印章也有些模糊,但那标志性的造型,尤其是酒标上那四个字——“汉帝赐福”——让她的手心瞬间冒出一层细密的冷汗。
李诚闻声从屋里跑出来,看到那个盒子时,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夫妻俩对视一眼,谁都没有说话。
空气仿佛被这突如其来的酒香抽成了真空。
他们一言不发,但心里都清楚,这场刚刚开始的平静生活,也许从这一刻起,再也回不去了……
01
苏晴是市郊一家国企单位的出纳,工作朝九晚五,稳定但薪水微薄,胜在清闲。丈夫李诚在一家私营汽配厂当车间主管,收入还算可以,但常年需要上夜班,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,几乎都压在苏晴一个人身上。
结婚五年,孩子上了小学,两口子一直开着一辆老掉牙的本田。那车有十多年车龄了,冬天打不着火是家常便饭,夏天空调吹出来的风比车外还热。年初的时候,车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彻底趴窝,这才让他们下定决心换车。
他们原本的计划,是在二手车市场淘一辆十几万的代步车,先凑合几年。但苏晴心里,总还是盼着能换辆好点的。直到有一天中午,办公室新来的小陶一边泡茶一边神秘兮兮地凑过来说:“晴姐,我听说咱们单位行政处的王主任想换车,他那辆奥迪才开了不到两年,成色新得很,好像说只要八万块就卖。”
苏晴听完就愣住了。
王主任?王建国?那个人在单位里是出了名的精明,对钱看得比什么都重,怎么可能把一辆几乎全新的好车用这种“跳楼价”处理掉?
她心里犯嘀咕,但脸上没显出来。回到工位后,她悄悄用手机查了一下那款车的二手市场价,普遍都在三十万以上。看着屏幕上的数字,她的心开始摇摆不定。
结果没过两天,王建国竟然在下班的停车场主动把她拦了下来,笑着拍了拍车顶:“小苏,听说你想换车?看看我这辆怎么样?成色绝对新,平时都是司机在开。我老婆嫌这车太大,开着不方便,我呢,也准备换个新能源,就想着赶紧出手。”
苏晴试探着问:“王主任,这车……保养情况怎么样?”
王建国摆了摆手,故作轻松地叹了口气:“全程都在4S店保养,记录你可以随便查。这不是我儿子马上要出国了嘛,家里又要添新车,手头一下子有点紧,不然我也不会这么着急卖。都是一个单位的,我还能坑你?给你个最实在的价格。”
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。苏晴回家跟李诚一商量,李诚立刻皱起了眉头:“你可别一听便宜就上头。这种事得多个心眼。他为什么不挂到二手车平台去卖?偏偏就便宜给你?这里头不正常。”
苏晴却不这么认为:“车我今天下午试驾了一下,开起来没任何问题,手续也都齐全。他真要是坑我,抬头不见低头见的,在单位里我还找不到他?再说了,买了他的车,以后在工作上,说不定还能多照应着点。”
第二天,她还在犹豫,单位里一个跟她关系不错的同事悄悄提醒她:“你要想买可得快点,我听说已经有好几个人约他看车了。”
这句话像一根针,瞬间戳破了苏晴的犹豫。合适的车太难找了,她跑了快两个月市场,都没碰上一辆真正中意的。现在突然冒出来这么一辆成色好、价格低、还是知根知底的单位领导的车,错过这个村,可能就真没这个店了。
她第二天一早就主动找到了王建国,两人很快签了份简单的转让协议,当场刷卡付了全款。八万块——苏晴觉得自己捡了个天大的便宜。
车子过完户那天,王建国亲自把车钥匙交到她手里,态度好得出奇:“车里的东西我基本上都清空了,就剩下点车载纸巾、一把雨伞和一个工具箱,也懒得拿了,就当送你了,你留着用吧。”
李诚知道后,脸上写满了不满:“你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定了?”
苏晴放低了声音:“你不是也说早该换车了吗?我真是怕再晚点,就让别人给抢走了。”
那天下午,两人一起把车从过户点开回家。坐在几乎全新的车里,仪表盘干净得发亮,方向盘上连一丝磨损的痕迹都没有。苏晴忍不住四处摸了摸,脸上是藏不住的笑意:“以后上班就开它了,这空调,可真给劲。”
李诚虽然对妻子擅作主张有些微词,但开着车回家的那段路,也确实觉得这车物超所值。他心里想,也许这一次,真的是自己多虑了。
02
夫妻俩很快就开始动手清理新车,准备做一次彻底的内外翻新。
车子整体保养得确实不错,车身漆面光洁,内饰也没有任何异味。方向盘、换挡杆这些最容易磨损的地方,都被细心地包上了保护套,看得出来前车主是个讲究人。
可唯独后备箱,看上去有些不正常的凌乱。侧边的衬板有些松动,底板下面用来放备胎的盖板,也翘起了一个小角,像是被人匆忙动过手脚,却没来得及复原。
苏晴和李诚商量了一下,决定先把后备箱彻底清空,把内衬重新整理一遍。李诚负责把那个赠送的工具箱搬出来,苏晴则戴上手套,从车尾开始清理一些零碎的杂物。
就在她拉开底板,准备把备胎上面的衬垫掀开的一瞬间,一块裹着厚厚灰尘的深灰色棉布,被从缝隙里带了出来。那布团微微鼓着,明显里面藏着什么硬物。
她警觉地喊了一声:“慢点……这个东西,看着不太像工具袋。”
小心翼翼地揭开那层布料后,一个老式的深棕色木盒显露了出来。盒子表面有些磕碰的痕迹,但封闭得异常严实。打开盒盖的那一刻,一股浓得化不开的酒香扑鼻而来。
盒中,稳稳地躺着两瓶包装陈旧、瓶身沉甸甸的白酒。标签虽然旧了,却依然能辨认出那熟悉的“茅台”字样。但与众不同的是,瓶身上还印着“汉帝赐福”四个古朴的篆字。
苏晴的心跳漏了一拍,她几乎是把那个盒子“抱”回屋里的,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。她打开电脑,开始在网上搜索这几个字。
搜索结果一条条跳出来,她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快要停滞了——
“汉帝茅台”,九十年代初期贵州茅台酒厂为纪念汉武帝“甘美之”的典故而特别推出的一款纪念酒。因其瓶身印有“汉帝赐福”的字样和图案,且发行数量极其稀少,几乎只在极小的内部渠道流通,从未公开发售,因此被圈内人称为“茅台中的天花板”。
记录显示,2019年,一瓶同年份的汉帝茅台在拍卖会上拍出了3100万的天价;而在2023年,另一瓶品相完好的同款酒,估价已经超过了6000万,并且有价无市。
李诚看到这些介绍时,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夫妻俩面面相觑,一时竟不知所措。
“这……这不会是王建国忘在车里的吧?”苏晴的声音有些发干。
“你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,听听他那边怎么说。”李诚盯着那个木盒,沉声说道。
苏晴点点头,立刻拨通了王建国的手机号。电话那头传来的,却是冰冷的系统提示音——“对不起,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”。
她不死心,又接连拨了两次,结果依然是关机。
第二天上班,她特意绕到行政处想当面问问,可王建国的办公室门锁着,前台的同事告诉她,王主任前几天就请长假了,说是要送孩子去国外念书,一下子就请了十天。
“也对,他当时卖车的时候就说是为了凑留学的钱。”苏晴勉强笑了笑,这样安慰自己。
可事情的走向,却在一周后发生了惊人的反转。
那天午休,她在单位食堂排队打饭,身后一桌的几个男同事正在低声议论着什么。
“你听说了吗?王建国好像不是请假,是出事了。”
“出事?不是送孩子出国了吗?”
“那是对外的说法,我听到的版本是,他被上面调查了。好像是牵扯了单位内部的一些烂账,领导层已经开过会了,决定直接免职。”
苏晴手里的餐盘“哐当”一声差点掉在地上。她顾不上吃饭,立马找了个相熟的同事核实情况。对方冲她点了点头,压低声音说:“是真的,上头的通知刚传下来,估计这两天就要正式发公告了。”
苏晴的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,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
他为什么会被突然免职?难道……难道跟这两瓶酒有关系?
她脑中闪过王建国交车那天过于平静甚至有些急切的神情。这两瓶来历不明的汉帝茅台,就像一根滚烫的细针,将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,狠狠地戳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窟窿。
从那天起,她再也联系不上王建国了。他的手机号一直处于关机状态,社交账号也不再更新,就连单位的工作系统里,也迅速地清除了他的姓名和工号。这个人,就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里一样,彻底从这家单位蒸发了。
几个老员工偶尔会在茶水间小声议论,说王建国早在出事前两个月就有些反常,经常一个人加班到深夜,还总盯着一个加密的U盘发呆。
“他走之前那几天,不是还把办公室的电脑全都格式化了吗?”
“我听说他那段时间,每天都在喝茶,但用的却是矿泉水瓶装的。”
这些零碎的信息,让苏晴心里的石头越沉越深。
那两瓶茅台,究竟是谁留下的?王建国为什么非要用一个低到离谱的价格紧急卖车?如果真的是为了儿子出国,为什么事后又像逃亡一样切断了所有的联系?
而更让她感到恐惧的是——这辆车,会不会也牵扯进了什么天大的麻烦里?
03
接下来的日子,苏晴和李诚过得如履薄冰。
他们总觉得那两瓶酒像是一个埋在家里的定时炸弹。也许哪天手机会突然响起,电话那头的人会冷冷地告诉他们,这辆车是涉案资产;又或者,会有人在半夜敲响他们的家门,面无表情地把那个木盒带走。
但奇怪的是,接下来的半个多月,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没有警察找上门,没有任何自称是失主的人联系他们,甚至连拍卖行、收藏家之类的角色也都没有出现。一切都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毛。王建国这个人,也像是彻底从人间蒸发了一样,再无半点音讯。
“越是这样没动静,我心里越不踏实。”
李诚坐在沙发上,一边翻看着手机地图上的车辆轨迹记录,一边喃喃自语,“如果这酒真值几千万,他怎么可能就这么忘了?”
他转过头,看着被临时放在客厅餐桌上的那个旧木盒,眼神里充满了怀疑,“你说,这酒……会不会是假的?”
苏晴也怔了一下。是啊,以王建国那样精明到骨子里的人,怎么可能会把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,随手就丢在一辆急于出售的二手车里?
“要不,我们找个懂行的人鉴定一下?”
两人一拍即合。第二天,他们带着其中一瓶汉帝茅台,悄悄地去了城南的古玩市场。
那里的巷子很深,门脸也都很旧,苏晴之前在网上查过,说这里藏着真正的高手。一番打听之后,他们找到了一家看起来毫不起眼、名叫“旧物斋”的小店。
“请问,郑师傅在吗?”苏晴站在门口,低声问道。
不多时,一位头发花白、戴着老花镜的老人从挂着布帘的内间走了出来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唐装,脸上没什么表情。他接过酒瓶的动作很稳,只是随意地扫了一眼,眼神就立刻变了。
“你们这酒……是打哪儿来的?”
李诚顿了一下,下意识地撒了个谎:“家里传下来的。我父亲年轻的时候,单位里有朋友送的,就一直搁在柜子里没动过。”
郑师傅没有追问,只是点了点头,戴上一副白手套,将酒瓶小心地放在铺着绒布的案台上。他打开一盏强光台灯,开始从封口到瓶底,一寸一寸地仔细检查。
他先是观察封蜡的老化程度和瓶口的螺旋纹,再用一个高倍放大镜对着瓶标,仔细检查上面的印刷细节。之后,他甚至轻轻地摇晃了一下酒瓶,侧着耳朵,像是要倾听酒液在瓶壁上流动的声音。
“封蜡收缩自然,没有二次处理的痕迹。纸标的压痕清晰,是九十年代特有的凹版印刷技术,油墨的颜色有轻微的褪色,但布局和字体都完全正确。”
他一边说,一边顿了一下,然后抬起头,看向他们夫妻俩:“从目前来看,这瓶酒,是真品。而且,酒体保存的状态非常好,几乎没有挥发。”
苏晴的心跳骤然加速,她用极小的声音问:“那……那它大概值多少钱?”
郑师傅沉思了片刻,缓缓说道:“如果是1995年出厂的汉帝茅台,品相完好,在正规的拍卖行,单瓶的起拍价,应该在三千万上下。”
他的话音刚落,店铺的内间突然传来一声轻咳,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年轻人走了出来,看样子像是拍卖行的助理。他走近看了一眼瓶身,随口问郑师傅:“汉帝茅台?您确定是真的?”
郑师傅点了点头:“真品。”
那个年轻人立刻露出了职业性的微笑,他转头看向苏晴和李诚:“两位,我这边可以直接收购,两千万现金,一口价。如果我们现在签协议,今天之内,钱就可以到你们账上。”
他的目光锐利,像是能直接看穿人心。苏晴和李诚对视了一眼,两个人的呼吸都像是停了一拍。
两千万。这个数字,对于他们这样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,太过惊人,近乎于一个天文数字。
他们在这座城市里辛苦打拼了十几年,掏空了所有积蓄,又背上了沉重的贷款,才勉强换了这辆二手车。而现在,仅仅是后备箱里的一瓶酒,就能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。
李诚感觉自己的喉咙一阵发干,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,说:“这个……是我父亲留下的遗物,我们得回去商量一下,才能做决定。”
离开古玩市场的时候,夫妻俩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李诚死死地拎着那个木盒,手背上青筋毕露。苏晴则控制不住地频频回头张望,总觉得身后有人在跟着他们。
他们没有直接回家,而是故意在市区绕了几个大圈,换了两次出租车,确信没有人跟踪之后,才最终拐回了自家的小区。
一进家门,苏晴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声音带着哭腔:“是真的……居然是真的……”
她冲进卧室,把那个装着天价茅台的木盒放在床头,整个人激动得浑身发抖。
李诚站在门口,双眼发直。
这个秘密实在太大了,大到他们一时间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
“你说……这酒,现在算是咱们的,对吧?”苏晴的声音还在颤抖。
“是我们的。”李诚用力地点了点头,“车是我们花钱买的,转让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,‘随车物品归买方所有’。他王建国连车里的雨伞都懒得拿,那没带走的东西,就理所当然不再属于他。”
两人反复用这句话来说服自己——他们没有偷,没有抢,这是明明白白的“合法所得”。
可就在那天晚上,两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,从睡梦中猛地惊醒。
他们听不到任何具体的声音,却都感觉到了一种同样的东西:一种无形的压力,一种仿佛有人正站在黑暗中,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们的凝视感。
窗帘在夜风中微微晃动,风声掠过楼宇的缝隙,发出的声音像是有人在低声耳语。
李诚压低了声音,说:“你有没有感觉……这家里,好像多了点什么。”
04
苏晴没有出声,只是把身上的被子裹得更紧了一些,像一个随时可能从高空坠落的人。
她也感受到了,那种目光。它不是真实存在的眼睛,却比任何真实的注视都更令人心头发毛。它好像就藏在天花板的缝隙里,藏在窗帘没有完全合拢的缝角处,藏在门下透进来的那一道细细的光线里,冰冷、克制、沉默地,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
几天之后,这种被窥视的感觉不但没有消退,反而越来越重。
他们在小区的电梯里,接连好几次碰见几个完全陌生的男人。他们穿着统一的黑色西装,皮鞋擦得锃亮,表情冷漠,只说是到顶楼去处理一点“公事”。楼下的停车位上,也莫名其妙地多了几辆黑色的轿车,车窗贴着极深的膜,从外面根本看不清里面是否坐着人。
苏晴变得愈发焦虑,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,吃不下饭,常常一个人对着门口的猫眼发呆。李诚也一样,有时候干脆就不睡了,一个人在客厅里抽烟,能从半夜抽到天亮。
那一晚,苏晴终于下定了决心:“我们把酒卖了吧。车也尽快处理掉,拿着钱回老家,或者干脆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……这东西,不能再留在身边了。”
她停顿了片刻,又补充道:“酒先藏好,我总觉得不安全。还是放回后备箱备用胎下面那个暗格里去,最好再用防水的袋子多包几层。”
李诚点了点头:“行。咱们这个小区又老又破,平时也没人会注意我们那辆车,藏回去反而更安全。接下来这段时间,我们必须万事小心。”
他们没有急于出手,而是选择继续和古玩行那边保持联系。交易的细节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。对方开价虽然很高,但也表现得异常谨慎,坚持要进行一次更严密的第二次鉴定。
对方在电话里明确表示:需要对瓶体进行微量的物理取样,检测酒体中的挥发物成分,并且已经邀请了北京一家知名拍卖行的首席鉴定顾问,专程飞过来当面确认。
这个要求让李诚立刻警惕了起来:“你说……他们会不会是在故意拖延时间,想套我们的话,最后再反咬我们一口?”
苏晴的神色也变得凝重:“现在的问题,已经不是酒是真是假了,而是这帮人,到底靠不靠谱。”
两人反复权衡之后,决定先给对方立一个规矩:可以进行二次鉴定,但必须先支付总价款20%的定金,作为交易的意向保障。
这个提议发过去之后,古玩行方面并没有立刻回应,而是表示需要内部讨论,征求一下买方的意见。
谈判由此陷入了僵持。连续一个星期,双方通过电话和邮件来回拉锯,但每一次都绕不开最关键的一步——谁先让步,谁就等于先亮出了自己的底牌。
直到第八天,对方突然松了口:定金无法支付,但如果鉴定结果无误,他们可以在原定的报价基础上,再增加一百万,作为补偿和诚意。
这个条件让苏晴和李诚都心动了。虽然不如预想的那么稳妥,但一百万的额外收益,足以抵消掉他们为此冒的风险。
第二次鉴定被安排在一家安保严密的老牌收藏鉴定所,郑师傅也一同到场了。
这一次的流程,远比上次要严密得多。他们先是使用了专业的荧光照射设备,来检查封蜡的老化纹路;然后又对瓶底的玻璃质地进行了成分光谱分析;接着,又仔细比对了标签印刷中的凹凸压痕;最后,甚至动用了高倍显微镜,来查看纸张纤维的氧化程度。
几位专家轮番上阵,操作谨慎,全程一言不发。
最终,专家组共同签署了一份联合鉴定报告,结论是:该瓶确认为1995年原厂生产的汉帝茅台,酒体无渗漏、封蜡完整自然、各项物理和化学细节均与官方留存的样本高度一致。
其中一位年长的鉴定师忍不住感叹道:“像这样品相完整、存放得如此完好的汉帝茅台,我从业二十多年,也仅仅只见过一次。”
直到这一刻,苏晴和李诚才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根据双方的协议,既然第一瓶酒已经确认无误,那么就可以将两瓶酒一并打包出售,总价为四千二百万。
当天晚上,他们决定把藏在车里的第二瓶酒也取出来,为第二天的正式交货做准备。
夜已经深了,风很冷。
一阵夹杂着地下车库特有潮湿气味的风从入口吹了进来,拂过脸颊,带着一种莫名的寒意。头顶的灯光昏黄,四周安静得仿佛能听见车辆引擎冷却时发出的“咔哒”声。
苏晴和李诚再次站在那辆奥迪车前。车尾的漆面上,已经落了薄薄的一层灰,像极了他们这几天的心境——模糊、沉重,看不真切。
他们动作轻缓,一言不发地打开了后备箱,将之前临时封回去的隔板重新掀开,然后合力撬起了那块用来隐藏酒的暗格底板。
熟悉的灰色布包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,纹丝未动,仿佛它从未被任何人发现过,仿佛它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充满不安的现实世界。
李诚缓缓地将那个木盒抱了出来,沉甸甸的分量在手中传来一种熟悉的触感,那感觉,就像是捧着一块能把人压得喘不过气的命运石板。他低头看了一眼苏晴,她点了点头,示意他继续。
他轻轻地打开盒盖,另一瓶酒同样静静地躺在丝绸内衬里,瓶身的光泽柔和,封蜡完好如初,没有任何裂痕或破损,就好像时间从未在它身上留下过任何痕迹。
“确认没问题。”李诚轻声说了一句,正准备把盖子合上,却发现苏晴并没有看向他,而是蹲在后备箱旁边,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空了的暗格底部。
她的眉头紧紧锁着,眼神也渐渐凝固了。忽然,她用极低的声音“咦”了一声,那声音里充满了惊疑和不确定,就好像被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勾住了视线。
“怎么了?”李诚抬起头问,语气里还带着一丝即将完成任务的轻松。
苏晴没有回头,只是伸出手指,在暗格的底板上轻轻拂去了一层积灰:“你自己过来看……这里,是不是有东西露出来了?”
李诚的心猛地一沉,立刻蹲下身,凑了过去。他将手电筒的光束压得更低、更近——
就在两块底板的接缝之间,一个极淡的纸边,若隐若现地翘起了一角。那纸的颜色已经严重泛黄,边缘也有些起毛,但依然保持着一个完整的形状,像是早年间那种牛皮纸信封被折叠后的一角。
那绝不是普通的信纸,更不可能是包装纸。李诚的呼吸猛地一滞,喉咙里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抽气声,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在手电筒惨白的光束下,他的脸色白得吓人。
他伸出微微颤抖的手,试图将那个纸角抠出来,却发现那张纸被塞得异常紧实,像是有人在很久以前,用极大的力气将它硬生生地塞进了这条缝隙里,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任何人发现。
“这……这根本就不是酒的事儿了。”李诚的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在摩擦,他甚至没敢把那个东西完全抽出来,但一个可怕的念头已经在他脑中成型。他瞪大眼睛,死死地盯着苏令,声音沙哑得变了调:
“这酒,我们不能卖了。因为这酒,它根本就不是主角,它只是……”
李诚没有把话说完,但苏晴已经懂了。她顺着李诚的目光,看着那个只露出冰山一角的牛皮纸信封,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一瞬间冻结了。
这酒,只是一个幌子,一个用来掩人耳目的、价值连城的烟雾弹。
真正重要的东西,是藏在酒下面的这个信封。
李诚的手指抖得几乎握不住手电筒,他深吸了一口气,用指甲奋力地将那个信封一点一点地从缝隙里抠了出来。信封很薄,但分量却出奇的沉。没有封口,里面的东西可以直接倒出来。
他将信封倒转过来,轻轻一抖。
滑出来的不是信纸,也不是文件,而是一张被折叠了许多次的A4纸,和一个小巧的、黑色的U盘。
苏晴捂住了自己的嘴,才没让自己尖叫出声。她想起了单位同事的议论——王建国在出事前,经常一个人盯着一个加密的U盘发呆。
就是这个吗?
李诚的手抖得更厉害了,他缓缓地展开那张已经出现多处折痕的A4纸。
纸上没有一个多余的字,只有一张打印出来的表格。表格的标题是《往来账目(内部)》。下面则是一行行的条目,每一行都清晰地记录着:日期、姓名、金额、以及一个简短的“事由”。
那些姓名,有些他们认识,是本市一些企业的头面人物;还有一些,他们虽然不认识,但从姓名前面的职位来看,分明是市里各个部门的领导。而那些金额,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,密密麻麻地罗列下来,触目惊心。
这哪里是什么账目,这分明就是一本详细到令人发指的行贿记录!
而那个U盘……
夫妻俩对视了一眼,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他们几乎可以肯定,那个U盘里储存的,一定是比这张纸更致命、更完整的证据。
“王建国……他不是忘了,他是故意留下的。”苏晴的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叫,“他知道自己要出事,他不敢把这些东西带在身上,所以他把车卖给我们……他觉得我们这种普通人,永远也不会发现这个暗格……”
李诚的脸色惨白,他猛地反应了过来:“不对,他不是觉得我们不会发现,他可能……是想以后再找机会拿回来。卖给单位里最不起眼的同事,车子就停在眼皮子底下,这是最安全的方法。”
“那……那古玩行那些人呢?”苏晴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哭腔,“他们是真的想买酒吗?”
“买酒?”李诚发出了一声冷笑,那笑声在空旷的地下车库里显得异常刺耳,“他们根本就不是冲着酒来的!他们是冲着这个账本来的!王建国出事了,账本却不见了,他背后那些人肯定急疯了!他们放出风声收购汉帝茅台,其实就是在钓鱼,看谁会拿着这两瓶酒出现!”
真相像一把锋利的冰锥,瞬间刺穿了他们所有的幻想。
什么天降横财,什么改变命运,从头到尾,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,一个巨大的、足以将他们碾得粉身碎骨的漩涡。而他们,就像两只被诱饵吸引的飞虫,一头扎了进来。
“那我们现在怎么办?”苏晴彻底慌了,她抓住李诚的胳膊,指甲深深地陷进了他的肉里,“报警吗?我们把这些东西交给警察!”
“报警?”李诚猛地回头,眼睛里布满了血丝,“你拿什么报警?你怎么跟警察解释这东西的来源?你说我们从一辆八万块买来的奥迪后备箱里翻出来的?谁会信?到时候我们不仅一分钱拿不到,还会被当成王建国的同伙一起调查!你别忘了,这张纸上的人,哪个不是手眼通天的人物?我们斗得过他们吗?”
苏晴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。
是啊,他们斗不过。他们只是这个城市里最普通的两个人,无权无势,像两粒微不足道的尘埃。而他们手里拿着的,却是一颗足以引爆一场大地震的炸弹。
李诚将那张纸和U盘死死地攥在手心,汗水浸湿了纸张,让上面的字迹都开始变得有些模糊。他抬起头,环顾着这个阴冷、压抑的地下车库,第一次感觉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绝望。
“不能卖,也不能报警……”他喃喃自语,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,“这东西,现在是我们的催命符。我们得想办法,把它处理掉,或者……用它来换一条活路。”
那一晚,他们没有回家。
他们开着那辆奥迪,漫无目的地在城市的环路上绕了一圈又一圈。车窗外的霓虹灯飞速地向后掠去,像一道道绚丽而冰冷的伤口。车内,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,只有沉重而压抑的呼吸声。
他们手里握着一个可以毁掉无数人的秘密,但这个秘密,也随时可能毁掉他们自己。
天快亮的时候,李诚终于把车停在了一个偏僻的江边。他掐灭了烟头,转头对苏晴说:“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从现在开始,我们必须假设,我们已经被盯上了。”
苏晴的嘴唇毫无血色,她点了点头。
“账本和U盘,必须分开藏。U盘里的内容我们还不知道,但肯定比纸上的更重要。”李诚的思路在巨大的压力下反而变得异常清晰,“我明天去买一个最普通的移动硬盘,把U盘里的数据复制一份出来。原件,我们得找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藏起来。”
“哪里是绝对安全的地方?”
李诚沉默了片刻,说:“银行的保险柜。”
他用一个陌生的身份,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,将那个小小的黑色U盘,连同那张写满罪恶的A4纸,一起锁了进去。钥匙,他配了两把,一把自己拿着,一把交给了苏晴。
“如果我们俩谁出了事,另一个人就拿着钥匙,把里面的东西交给纪委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,表情平静得可怕。
苏晴接过那把冰冷的钥匙,感觉它像一块烙铁,烫得她手心生疼。
回到家,李诚立刻将复制了数据的移动硬盘连接到了电脑上。为了安全,他甚至拔掉了网线。
移动硬盘里只有一个加密的压缩包。李诚试了几个王建国可能会用的密码,比如他的生日、车牌号,都提示错误。
“他既然敢把这东西留下,密码肯定不会那么简单。”苏晴在一旁轻声说。
李诚没有放弃,他开始回忆关于王建国的一切细节。他想起小陶说过,王建国每天都喝茶,但用的却是矿泉水瓶。他突然灵光一闪,在密码框里输入了一串数字——那串数字,是单位附近那家矿泉水水站的电话号码。
屏幕上,进度条开始移动,压缩包被成功解开了。
里面的文件,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得多,也恐怖得多。
除了那份纸质账本的完整电子版,还有大量的照片、录音和视频。照片的场景大多是在各种高档的酒店、会所,内容不堪入目。而录音和视频,则清晰地记录了王建国和那些“大人物”之间关于利益输送的对话,时间、地点、金额,每一个细节都清晰无比。
王建国,这个在单位里看似精明的行政处主任,实际上是一个庞大腐败网络的核心枢纽。他不仅负责记账,还负责用这些肮脏的手段,将网里的每一个人都牢牢地捆绑在一起。
苏晴只看了几分钟,就感到一阵阵的反胃和眩晕。她冲进卫生间,吐得昏天黑地。
李诚则一言不发地将所有文件都看完,然后默默地将移动硬盘拔了下来。他的脸上,是一种混杂着恐惧、愤怒和一丝疯狂的表情。
“这些人,每一个都该死。”他低声说。
“我们……我们现在该怎么办?”苏晴扶着墙壁走出来,声音虚弱。
“等。”李诚说,“等对方先出牌。他们既然能找到古玩行来试探我们,就说明他们还不知道东西在我们手上。他们在暗,我们也在暗。现在,就看谁先沉不住气了。”
然而,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太多“等”的时间。
第二天,苏晴去上班,单位的气氛明显变得有些诡异。几个平时和王建国走得近的同事,看她的眼神都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探究。午休时,人力资源部的领导还特意找她谈话,旁敲侧击地询问她购买王建国那辆车的具体细节。
“小苏啊,王主任那辆车,你买的时候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吧?比如……车里有没有留下什么他个人的重要物品啊?”
苏晴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但脸上还是强装镇定:“没有啊,车里很干净,王主任交车的时候说都清理过了,就剩下点纸巾雨伞。”
领导笑了笑,那笑容却让苏晴感到一阵寒意:“那就好,那就好。毕竟是涉事人员的资产,我们也是按规定问一下。”
下班的时候,她发现那辆停在楼下的奥迪,左侧的后视镜上,被人用红色的油漆笔,画了一个小小的叉。
她吓得腿都软了,立刻打电话给李诚。
李诚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,然后用一种极为压抑的声音说:“他们知道了。他们在警告我们。”
那一天,他们没有敢回家。李诚让苏晴带着孩子先去酒店住下,他自己则开着车,在外面不停地兜圈子。他知道,家已经不再安全了。
深夜,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。
李诚犹豫了一下,还是接了。
电话那头,是一个经过处理的、听不出男女的声音:“东西,在你手上吧?”
李诚的心脏狂跳,但他还是稳住了声线: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
“呵呵,”对方冷笑了一声,“年轻人,不要自作聪明。王建国那辆车,从他卖给你的那一刻起,就一直在我们的视线里。你们去古玩行,去银行,我们都一清二楚。我们只是想给你一个机会,让你自己把东西交出来。”
李诚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了。原来,他们根本就不是在暗处,他们的一举一动,都早已暴露在对方的监控之下。
“你们想怎么样?”李诚的声音有些沙哑。
“很简单。把你手里的东西,原封不动地还回来。我们可以给你一笔钱,足够你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,然后送你们离开这里,去一个没人认识你们的地方。这件事,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。”
“我怎么相信你们?”
“你没有选择,只能相信我们。”对方的语气变得冰冷,“或者,你也可以选择报警,看看是你先拿到所谓的正义,还是我们先找到你的妻子和孩子。你是个聪明人,应该知道怎么选。”
电话挂断了。
李诚握着手机,手抖得像筛糠。他看着车窗外这座他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,第一次感觉它是如此的陌生和危险。
他没有退路了。
他拨通了苏晴的电话,将对方的条件说了一遍。苏晴在电话那头沉默了,许久之后,才带着哭腔说:“李诚,我怕……我只想和孩子平平安安地活着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李诚闭上了眼睛,“我也是。”
他知道,这是一场豪赌。赌赢了,他们带着一笔巨款远走高飞;赌输了,万劫不复。
他按照对方的要求,将复制了数据的移动硬盘格式化,然后用一个新手机,回复了一条信息:“我答应你们。但钱要先到账,一半。另一半,等我把东西交给你们之后,再付清。”
他必须为自己争取一点主动权。
对方很快回复:“可以。给你一个海外账户,明天早上八点,你会收到五百万。剩下的,等你交出东西和银行保险柜的钥匙后,一分不少地打给你。”
第二天早上,李诚用公共电话亭的电脑查了那个账户,里面不多不少,静静地躺着五百万。
钱是真的。
对方的“诚意”,也是真的。
交易的时间,定在了当天晚上。地点,是城郊一个已经废弃的烂尾楼盘。对方要求他一个人去,不能带任何通讯设备。
出发前,李诚最后一次拥抱了苏晴和孩子。
他对苏晴说:“如果我晚上十二点还没回来,你就拿着那把钥匙,去纪委。不要管我,带着孩子,走得越远越好。”
苏晴哭着摇头,却被李诚坚定地推开了。
他独自一人,开着那辆奥迪,驶向了那个未知的、可能是地狱的深渊。
烂尾楼里一片死寂,只有风穿过空洞的窗户时发出的呜咽声。李诚按照指示,将车停在了地下车库。他刚下车,就被两个穿着黑衣的壮汉围了上来,蒙上了眼睛,带进了一部电梯。
电梯升了很久,停下。他被带进一个房间,眼罩被摘了下来。
房间里只坐着一个人,就是那个曾经在古玩行里见过一面的、穿着西装的年轻人。
“郑师傅呢?”李诚下意识地问。
年轻人笑了笑:“郑师傅年纪大了,不适合参与这种事情。他只是个负责鉴定真伪的专家而已。”
他的身后,站着两个面无表情的保镖。
“东西带来了吗?”年轻人问。
李诚从怀里掏出那个小小的黑色U盘,和那把冰冷的银行保险柜钥匙,放在了桌子上。
年轻人拿起U盘,插进身边的笔记本电脑,仔细地核对着里面的内容。他的表情很专注,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。
几分钟后,他点了点头,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:“很好,东西都在。和你这样聪明的人合作,就是愉快。”
他打了个响指,身后的一个保镖拎过来一个黑色的旅行箱,放在桌上,打开。里面是满满一箱子崭新的美金。
“这里是五十万美金,加上之前打给你的,足够你们在任何一个国家过上富裕的生活了。”年轻人说,“我们还为你们准备了新的身份和护照,以及今晚飞往东南亚的机票。从现在开始,李诚和苏晴这两个人,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”
他将一叠证件和机票推到李诚面前。
李诚看着那些陌生的名字和照片,心里五味杂陈。他赢了,他用一个足以掀翻整座城市的秘密,换来了家人的安全和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。
但是,他真的赢了吗?
就在他准备拿起箱子和证件的时候,年轻人突然又开口了:“哦,对了,还有一件事。”
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,和一支笔。
“签了它。”
那是一份自白书。上面的内容,是承认李诚自己,才是王建国腐败案的真正同伙。是他,利用职务之便,长期协助王建国进行敲诈和勒索。而王建国手里的那些证据,也全都是由他保管。
“你……你们这是什么意思?”李诚的脸色瞬间变了。
年轻人脸上的笑容变得有些狰狞:“没什么意思。只是需要一个替罪羊而已。王建国已经被我们送出去了,这个案子总要有人来扛。你放心,这份东西我们暂时不会用。只要你和你的家人在国外安分守己,它就永远只是一张废纸。但如果你们敢耍什么花样……”
他没有把话说完,但那威胁的意味,已经不言而喻。
李诚的拳头,在身侧死死地攥紧了。他看着对方那张年轻而冷酷的脸,终于明白,自己从头到尾,都只是这盘棋局里的一颗棋子。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放过他,他们只是想用一种更“文明”的方式,让他永远地闭上嘴。
签,还是不签?
签了,他就要背上一辈子的黑锅,像一只被拴了链子的狗,永远活在对方的掌控之下。
不签,他今晚可能就走不出这栋烂尾楼。
时间,一分一秒地过去。房间里的空气,仿佛都凝固了。
最终,李诚缓缓地拿起了那支笔。
他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在落笔的那一刻,他感觉自己身体里的某种东西,被彻底抽空了。
他拎着那个沉重的箱子,拿着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身份,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,被送出了烂尾楼。那辆奥迪车,钥匙还插在上面,但他知道,他再也不能开它了。
一辆黑色的轿车,早已等在了路边。
车子载着他,去酒店接上了早已等得心急如焚的苏晴和孩子,然后一路疾驰,向着机场的方向开去。
一路上,夫妻俩都没有说话。孩子在苏晴的怀里沉沉地睡着,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命运,在这一夜之间,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。
飞机起飞的时候,李诚透过舷窗,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城市的灯火。那些曾经熟悉的光芒,此刻在他的眼里,却显得那么的遥远和不真实。
他逃出来了,带着钱,带着家人。
但他失去的,却是自己的名字,自己的过去,以及……那份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安稳和尊严。
几个月后,在异国他乡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上,李诚从网上看到了一条来自国内的新闻。新闻很短,说本市的一起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成功告破,主犯王建国畏罪潜逃,其重要同伙李某(男,35岁,某汽配厂主管)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主动投案自首,并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,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。
他默默地关掉了网页,转头看向窗外。
窗外是蔚蓝的大海和金色的沙滩,阳光明媚,岁月静好。
苏晴从身后轻轻地抱住了他,将头靠在他的背上。
“都过去了。”她说。
李诚没有回头,只是低声地问:“我们……真的自由了吗?”
这个问题,没有人能回答他。
他们拥有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财富,却也背负上了一个永远无法与人言说的秘密。他们是幸运的逃亡者,也是被命运流放的囚徒。未来的路还很长,但他们知道,他们再也回不去了。
你觉得,他们用自己的良知和过去,换来的这种“新生”,值得吗?
如果换做是你,你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?
日照股票配资,炒股配资知识,股票配资平台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